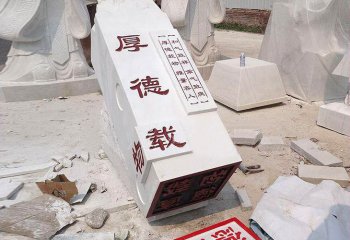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在此之前说一下关于人们对艺术家的追捧,任何艺术作品,有喜欢的就必有不喜欢的,有追捧的就必有被骂的。而且在个性鲜明的艺术作品更是如此,个性的本质就是排他。即使如印坛巨擘齐白石也有骂他是野狐禅的。因此题主不必在意别人怎么吹捧,只需要直视你自己喜不喜欢就够了!

以下是我的观点:篆刻和书法一样在发展,到了现当代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艺术家新的很先锋的作品,看得懂也好,看不懂也好,作为探索的作品总有其存在的价值。任何一个新事物从产生到时间的打磨沉淀,都需要一个过程,在淘汰中,不好的自然被冲走,好的会逐渐浮起来。
写意印和工稳印重点不一样,写意印追求一种意趣,追求一种偶然的恰到好处,兴之所至提笔奏刀,结构的自然不对称,章法的出人意料以及有刀有笔尤有刀笔之外的艺术效果,更多的是感性情感的流露。工稳的印总需要反复设计,更多的是理性的思维。题主所传的图,是书法篆刻界的名人曾翔的作品。他是个不走寻常路的艺术家。鲁迅先生说这世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艺术的创作也是这样,主流的大路既好走也难走,难走在于拉不开距离。另辟蹊径的小路既难走也好走,难在于荆棘密布,这荆棘不仅在于艺术本身的难题需逐一解决,还在于主流价值观的不认同。
然而,虽是小径走的人多了也慢慢成为大道坦途。总需要有一个人开始走这样的小径。佛像印系列,我也看不太懂,但是从效果来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现当代的艺术,是趋于观观念的艺术,观念先行,也就是说怎么想指导怎么做。不再是早些时候文人书法篆刻时候比较看重自然而然的流露。观念的艺术,更加刻意,我说刻意没有贬低的意思。首先要的就是观念新颖,不与人同,这时候其实没有办法考虑好还是坏,第一考虑的是得做出作品来,做出来了就成功了一半。
观念的艺术是尝试的艺术,而尝试有成功有失败,无论成功与否,其探索都是有意义的。观念的艺术不太注重日积月累的自然而然,日积月累的艺术其本质是时间的艺术,一丝一毫的慢慢变化,重功夫与技巧。而观念则是刻意的跳出来,以想法为主,是思考能力的艺术。说到底也许大多数人都可以去做,但他们又不会去做,因为压根儿他们就不会这么去想。艺术之所以会发展,不是完全靠日复一日的熟能生巧,靠的必须是观念。
观念不变则艺术一层不变,做得好还能够保持前代遗留,不好则成为我们说的今不如古,江河日下。在我们的传统里以为今不如古是主流价值观,因此但凡有创变则有来自古法古制的压倒性打压。艺术的发展从来都是在逆境中寻找希望。孔子的理想社会在西周,而篆刻界同仁们长期推崇的是印宗秦汉,书法界长期占主流的是二王米芾。陶印系列,由于材质的特殊性,更加适合表现率意一点的风格,从印拓效果来看,手法是划加上刻的综合运用,结构也是如同孩儿体一样的,不追求优美,追求稚与拙。
同时他还加入了一些文字之外的划痕来营造一种效果。如果以传统文人印章追求雅化的标准来看则失偏颇。实际上曾翔的刻法也是取法前人,只是并非学主流而已。印章里面早就有滑石印,书法刻石里亦有,尤其是刑徒砖和陶文。
其佛像印系列或也受到刑徒砖文的启发。刑徒砖陶文陶文原刻滑石印由于是古代工匠草率刻制,多是直接凿刻,而且多是正刻印出来则是反的。这样的印更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不在技法,而在趣味,那种无意于佳的美感。就如龙门的刻石和摩崖,早期极少甚至是没人去学习取法的,而到了清中晚期学习的书家就多了。
没有审美观念的改变,我们大抵还在唐碑中徘徊,在看似大道坦途的路径上绞尽脑汁而无法跳出来。以上所举皆是古人无意为之,而曾翔则是把这种无意变成有意,进而成为他的创作手法,因之这些材料也就成了他取法的源泉。书、印、画,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东西。大多数人的审美,习惯于立足判断,即“这是什么”?
如果能找到一个肯定的、合理的答案,才可以继续下去。比如欣赏一幅画,首先都要判断一下——这画的是啥?然后是像不像。如果无法判断是啥,或者像不像,就无法继续欣赏了。涉及到书法、篆刻一类,也不自觉地套用这类模式——写得是啥?像不像一副好字?呵呵。
但,有时候,不妨来看看“热闹”,这样反而更有趣。就像问题中的图,非要看破是个啥么?这些线条、这些体积本身不是更有趣么?管它是个啥,看出自己的趣味来,不亦乐乎。这是大佬嘛,线条这样轻浮,功力没迈入门槛。把碑理解的太浅太浅了。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这种水平的说不明白。丑到无与伦比,再多的夸赞,都是睁着眼睛胡说八道。
这种东西,完全是视觉污染,不看最好!前人是無意於佳,而這些是有意於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