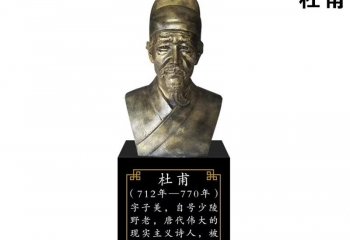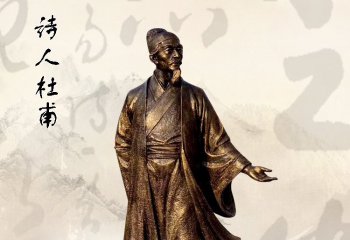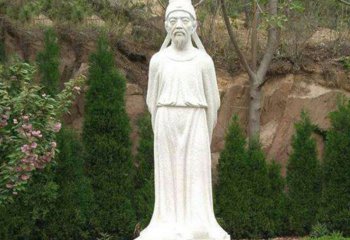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我们跨过了王维、孟浩然这样的和山川草木为伴的人,来到了杜甫面前。杜甫是谁?唐诗断代分为四种,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作为盛唐到中唐的一般的标志就是杜甫的去世。

杜甫承接着盛唐的繁华,又见证了一段周而复始的乱世。我们从一个老者的身影讲起,这一年,饥饿和贫穷是他最熟悉的朋友。他离开了安稳的成都,顺着长江而下,他来到了长沙,居无定所。此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两年而已。他站在了著名洞庭湖旁,登上了那座天下闻名岳阳楼。
流水和高楼本来就是唐诗高频出现的意象,人生的时间如水,流逝不返;人生的境遇如楼,登高望远。洞庭湖和岳阳楼留下许多诗人的踪迹,孟浩然见到洞庭湖写下“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李白登岳阳楼写下“楼观岳阳尽,川向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在杜甫之后,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名句“欲为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阳楼”,同样是把洞庭湖和岳阳楼和人生际遇的心境对应起来。
当然,岳阳楼更为出名要等到几百年后,宋朝宰相和诗人范仲淹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岳阳楼在唐朝这么热门,得益于它的扩建正是由于一名诗人的到来,和盛唐息息相关。唐玄宗开元四年,宰相和诗人张说被贬为岳州刺史,他很喜爱临洞庭湖眺望,便招聘名工巧匠将一座湖边的古迹岳阳楼扩建楼阁,才使岳阳楼的名气传播开来。
诗人们谈岳阳楼还有一层意思,这是盛唐初年的建筑,是那个“忆昔开元全盛日”的代表。杜甫是完整经历过唐朝由极盛转为衰败的诗人,时不我与、睹物思人,想到那个强盛和繁华的唐朝就这样一去不返,自己的年华、理想也随其顺流直下。这才有了这首《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昔日听到的那个洞庭水和今天看到的洞庭水可能没有区别,但今天上楼的人却不是那个意气风发要当国士栋梁的人。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春秋的诸侯国吴国、楚国都是往日的传说,这两个国家本来并不是同时存在的国家。但诗人把他们的位置联系在一起,他们一个在东,一个在南,好像是因为这个洞庭湖而分裂。这是跨越时间的上帝角度,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看的大气魄,非人眼能看到的场景。“乾坤日夜浮”,天地和日夜都浮在这片静静的水面上。一个“坼”,一个“浮”,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一种漂泊和临时状态。
这是借古人和眼前的景象舒缓自己内心的愤懑,此时的唐朝因为战乱又何尝不是各地分裂,乾坤颠倒。杜甫这首登楼之作没有任何一个字来写美景风物,此刻的风景没有变,但诗人眼中没有审美的心情,有的只是一副垂垂老矣的病身,和舒展不开的愁容。“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亲朋好友不是没有一个人,而是无一“字”,这比“无一人”更能凸显出那种孤独中的思念之情,如果是“亲朋无一人”,是客观描述,但我们体会不到诗人的感情。“无一字”意涵就更深了,一个字就将这个故事的情感空间扩展了数倍,这就是“一字师”,这一个字的功力抵得上很多诗人一生的努力。
人生最大恐惧的死亡,死亡的恐惧是什么呢?就是“老”和“病”,如果比“老”和“病”更进一步的恐惧是什么,只有“孤独”了吧。“老病有孤舟”写尽了一个人的悲惨晚年。人生已经走向这样的绝境,生活已经困苦到极点。
杜甫把心还是交给了国家。他在诗的最后一句没有写自己的心情,怜惜自己,眼泪和悲伤没有留给自己,而是把更深的感情和希望给了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他没有为自己哭,默默为国家留下了眼泪。
这就是杜甫的一生,他用诗歌记录了他心中最重要的东西——对国家,对天下的责任和使命。如果说李白是一个永远的少年,那么杜甫就是永远的士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模板样本。我们对比下西方基督教文明对于个人的重要意义,来自于人是和神直接沟通的,婚姻的神圣性也是模拟了敬神仪式,西方基督教婚姻誓词里说“无论顺境或逆境、贫穷或富有、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着你”。但在中国古代,家庭是家族秩序下的一个小团体,家族是国家秩序下的单位,中国古代家庭对彼此的情感责任更多出于秩序和情感,而非责任。
如果我们把这段话用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他们的情感主题就会是自己的国家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