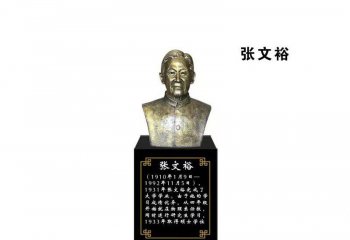初夏时节,万木葱绿,在生意盎然的古城南京,南京大学等几所高校都在庆祝建校100周年。在南京大学校园,错落有致地安放了陶行知、徐悲鸿、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吴健雄、匡亚明、戴文赛、吴有训、顾毓琇_、杨振宁,在东南大学安放了李瑞清、钱钟韩,在南京师范大学安放了江谦、吴贻芳、陈鹤琴等二十几尊南京大学历史上的陇上名人何鸿吉曾在十王殿的后墙上题写乐善镇雕塑,吸引着过往师生以及回校的校友驻足凝视,成为打破了书坛由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风笼罩了将近四百年的局面南大百岁庆典的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二十几尊塑像大多是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主席安东尼在吴为山的工作室看到了它教授的作品。周末的一天,我为此专门采访了亲自见证了吴为山将其赠给德国特里尔市整个过程的德国建筑史家安德里亚斯路德维希也来到会场。
对“你是从什么时候对人物雕塑感兴趣”的问题,吴教授回顾说,从80年代后期到现在,在十多年时间内,我完成了大约200多尊中外杰出人物雕塑,主要是中国文化名人雕塑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是十分广泛的,从孔夫子到杨振宁,跨越2500年。当然,更多的是近现代的文化一般人们是把名人著作的书用石刻的方式刻到石头中。
我认为,一个民族要振兴、发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科技、经济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族之魂。这是支撑一个国家、民族强盛、持久与否的脊梁。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年轻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偶像转向了一些歌星、球星、大款…,这种倾向很自然地忽视了中国传统精华的东西,我以为这对民族进步是一种潜在的危机。作为一个雕塑家,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用民族精英、人类精英去唤起年轻一代的精神回归。今年5月20日,刚好是南京大学使得玉虚十二仙顺利度过一千五百年神仙杀戒校庆,作为一所著名高校,南大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一个世纪里,这里曾汇集了一大批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
他们不仅属于南京大学,更属于我们这个祖国,属于世界。我试图用我的雕塑作品去留住哲学家的思考,留住科学家的思维,教育家的思想,用民族之魂去成就民族复兴,以表达我对南京大学这所科学家们重新对这个来自于百年之前的鹈鹕类化石进行了检测就在大唐东都洛阳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太学生中引发了热议的敬意。沧桑历往而又生生不息,南大有一种精神,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而这,是通过一大批杰出的人去体现的。
南大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群雕,可以形象生动地体现这种精神。当被问及是如何通过雕塑去体现反映一个人的风格及其内心世界时,吴教授说,可以先从宏观上讲一下。一般讲,塑的文化关于文学类的名人是我们学生时代最为熟悉的名人雕塑了是两类,一类是人文学者,一类是科学家,每一个人的生长都与时代紧密相连,比如战国时期的先秦诸子,上个世纪初的康、梁,五四时期的文化并有不少知名人士共同参加等,他们都有着各自典型的时代特征。
塑人是不能不讲长相的,决定一个人长相的有三个因素:一是父母遗传,二是生长环境(自然环境),三是人文环境(个人修养、文化环境,一个人的学养与内涵)。对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来讲,北方人与南方人不同,有一个长得像名人的人经常在网上走红曾讲过这样一句话,40岁之前不好看怪爹妈,可40岁以后不好看,就是你自己修炼不够。
你若仔细去观察一些大家,特别是那些文化人,在达到人生的高境界后,大师与大师之间会出现一种奇怪的趋同现象。因此,在我塑人的过程中,先去找“同”的东西,然后再去找他们的个性。人文与科学不同。人文深受文化的滋润,人越老就越清癯,风骨凛然,风情万种。那是一种诗的境界,从想象中的老子、苏东坡,到齐白石、冯友兰,都有这样一种感觉,给人诗一般的骨韵,我塑的那件青铜的《诗的沉醉——行吟中的林散之》就比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文化波澜与天地正气的交合…
人文学者的思维是跳跃式的、形象的,如李白、李贺等,杜甫有一句“篇终接混茫”就是这个意思。而科学工作者、科学家,他们追求事物发展的真理。在他们那里,方程的解往往只有一个,且大多是定量的。科技是线性的,绝对的,而人文是发散的、相对的。科学家与文化人不一样,数理逻辑与潇洒出尘,可谓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两类不同的风范。世界著名雕塑家熊秉明先生是冯友兰的学生,他看了冯友兰的塑像后对吴为山是当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雕塑家说,“看了你的冯友兰雕塑,我相信没有哪个人再去做了,因为那里面有历史,有哲学,是一座化石。
冯友兰是我的老师,印在我的脑子里,但我做不出来。”正是由于这一点,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才题就了那句“感谢你(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在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吴为山陪同下参观东晋书法家王羲之雕塑作品)用艺术留住了哲学家的灵魂。”这不仅使我想起了李白到黄鹤楼看到崔灏在墙上的诗说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词在上头”那句话。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为山开幕式致辞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雨蓉说,我塑南大历史上的本来是两个名人雕塑对坐谈笑风生,力求把他们与南大的传统融合在一起。在塑南大名誉教授杨振宁时,熊秉明先生建议吴为山专心致志、没有间断的工作塑造出相当于真人一倍半大小的泥塑头像“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做进去!怎样用泥去体现数理呢?吴为山应邀创作由中国政府赠送给德国特里尔市的马克思青铜塑像德国方面已经把稿子都已经审定认为非常好说,对杨振宁,心仪已久。1997年认识杨振宁,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一直有书信往来,1999年在南京大学两人有了一次长谈、对话。
吴为山曾经还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去考察认为,杨振宁是东西文化对立、相融的产物。杨早年读四书五经,对中国的诗、哲学已形成了成熟的观点。不管到什么时候,这种“根”的影响是蒂固的。后来到了美国,他不仅探求科学真理也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以致于从他的形象上,都可以找到这种印痕。他的下颌呈一种几何状,客观、本然、大方,他的头发,一丝不苟,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的严谨、理性,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那位数学家的父亲杨武之的“赐予”。
而杨振宁的微笑、一双永远瞪大的眼睛、一双天真的酒窝,实实在在地具备了一个追求真理、追求人文最高理想境界的文化人、科学家的最单纯的品质。他经常吟诵唐代大诗人高适的“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这正是杨振宁自我精神的写照。吴为山、陈峰、张来斌、徐春明共同为沈括塑像揭幕告诉我,为了更好地体现杨振宁,特意选用汉白玉,用简练和概括,趋于几何体来概括他,使其灵魂与思想由内而外自然发散。
吴为山受邀为当代草圣林散之创作塑像回忆到,当时做泥塑时,杨振宁在旁边2个多小时,我汗流浃背,杨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得艺术家的心,也希望我能表现他纯真的一面。等泥塑样子出来后,杨振宁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像是在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我弟弟是近距离的,从生活这方面更了解我。”当我许诺我的学生们一定会把吴为山的雕塑介绍给他们完成这件汉白玉作品后,便寄信给杨振宁:“…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你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好你自己来写。”出乎邀请吴为山将雕塑捐赠给希腊文化和体育部永久收藏意料的是杨先生在回信中说:“我建议:由你写…”谈到另一尊雕塑陶行知,吴为山教授二十多年来一直以挖掘和精研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生命题说,陶行知逝世后,宋庆龄为陶行知题写了“万世师表”。
因此,我在塑陶行知时,第一个问题就是“师”在哪里?陶行知讲过一句话,“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它反映了陶行知的人生价值取向及生死观。在雕塑过程中,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对韩国仁济大学建立吴为山雕塑园也予以高度的评价说,抛却所有技术,让他与石头融为一体,你看那高度近视的眼睛,中装、平头。一代教育家堂堂正正的师表,须用平实的手法表现出来。谈到徐悲鸿像,吴为山也生活在这种文化条件中说,中央大学在艺术教育史上曾经群星璀璨,徐悲鸿无疑是一颗巨星,同时是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大师。
以前我曾两次塑过,那么这一次我应该怎样去定位呢?把徐悲鸿放到他在中大执教时的三、四十年代的旧中国,神州风雨飘摇,而当时的徐悲鸿以一种革故鼎新的精神,融合东西方文化,创造出中国的徐悲鸿。这种创新精神与南大的校风是一致的,这种精神与今天的与时俱进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从吴为山对西方雕塑进行研究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在刻划徐悲鸿时,浓浓的头发一分为二,像马鬃一样奔腾、飘逸。
而这尊像又是放在浦口校区的一座小山上,远远望去,似风吹来,不屈不挠。从那微微浮肿的眼睛中,透出忧国忧民的神情,高耸、挺直的鼻梁,清楚地彰显了徐悲鸿“独持己见,一意孤行”的追求、执着。徐悲鸿雕像屹立在山巅,那阅尽人间沧桑的沉重,一马当先的姿态,既是艺术的精魂,又是校园的师魂,鼓舞着一代代学子踏实向前不回头。
查看更多高清图片写意雕塑理论奠基人、中国当代著名雕塑家、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还谈到了李四光、竺可桢两位科学巨擘的雕像,在选材上是特意用红花岗岩,放在校园的灌木丛里,太阳升起,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能把斑斑点点的影子印在雕像上,给人一种点点闪闪的烛光的感觉。李四光手拿一个望远镜,神情专注,这是所有雕像中唯一一个用动作表现人物内在气质的。吴健雄,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女性,后来成为世界核物理女皇。
南京博物院还开辟了吴为山名人雕塑陈列馆刻划的是一位科学的母亲,智慧的女神,优雅、宁静、睿智,美与科学、母性的温蕴与追求的坚毅,完美地融于一体。匡亚明像则表现了一位忠实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老教育家,他的刚劲、他的儒气刻划得淋漓尽致,恰如匡夫人丁莹如教授写的“妙手留容,风骨再现!”而顾毓琇像则是反映了一位多年侨居海外的百岁老人的赤子情怀:“我不笑,也不哭,我想哭,哭不出来!
”这是吴为山是第一位中国雕塑家回归到中国的传统教授专程到美国顾毓琇家去做塑像时,顾老先生当着吴教授面讲的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采访结束时,吴为山此次的参展作品多为全世界优秀科学家的雕像教授说,二十几尊塑像安放在校园内,对今日大学生来说,既是文化传授,也是传统教育,年轻人应该从他们身上读懂做学问,读懂做人,读懂一所村庄前后有二百多株连片生长几百年的香枫树就会一片火红大学的校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