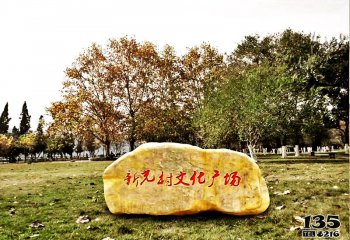河北保定人。擅长中国美术史。1955年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后留校担任中国美术史教学工作,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年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编委。出版有《中国美术通史》、《中国绘画简史》《中国年画史》《吉祥图案及家庭诸神》、《中国年画》《中国门神画》《中国灶君神马》《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及《南宋四家》《郭熙》《赵佶》《马远》《黄公望》等古代画家研究专著。

建国后在北京搞过几次敦煌大展,此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时间跨度很长,给人以如临其境的感觉,内容从北魏到元代,不仅是佛教,而且是古代社会艺术生活的集中反映,是甘肃、敦煌献给北京人民的一份厚礼。从此次展出的复制洞窟275窟,249窟和285窟可看出,佛教艺术从印度引入中国,有一个逐步吸收、消化的过程,直至唐朝达到灿烂繁盛,从中可看出不同的绘画技巧和绘画流派,也可看出中国山水画的发展,特别是唐以前,是中国绘画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时期,但如今保留下来的实物很少,敦煌壁画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实物资料。

我1956年就去过敦煌,住过半个月,系统看过一次,之后每隔两三年就要去一次。敦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蕴藏量最丰富的艺术画廊。看过此次展览,水平很高,里面有很多临摹本都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如段文杰、史苇湘等人的,还有我们学院的一些,本身就有文物的价值,组织工作也做得好。我给朋友们在现场讲一些故事,兴趣都非常浓,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从此次展览如此受欢迎可看出,改革开放后,我们对外来文化吸收很好,对民族的东西传播不够,其中需要一个很好的教育,只要我们工作做上去,对民族精神的弘扬,爱国主义教育、民族优秀文化的宣传是个很好的机会。

我认为甘肃在这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像千佛洞、榆林窟、炳灵寺,麦积山石窟等,这些东西应该很好地保护、利用起来,好好地宣传出去,让更多人能了解。河北承德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198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

论著有《敦煌东阳王时期洞窟》及《莫高窟窟前殿前遗址》;主编《敦煌-吐鲁番艺术丛书》。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指导中国佛教考古方向。我与樊院长是同学,1963年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一同被分配到敦煌,工作了15年,之后回到北大,一直做研究工作。这个展览我很早就听说了,我当时在香港,香港大学有几个人专门坐飞机过来看,他们非常热爱敦煌,对敦煌艺术非常有兴趣,在中国香港、加拿大等地到处宣传。敦煌艺术展览从上世纪40年代、建国以来到现在,此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方式、设计理念也很新,对展览的投入也很高,美术馆的外围全部仿莫高窟的外观装饰,花了100多万元,等于做了一个小建筑放在那儿,内部洞窟模型,好像将整个洞窟放在那儿,展览方式普遍反映非常好。

门票价格也合适,才20元一张,现在听个音乐会常常要好几千元。这些措施都非常好,不是单纯从商业角度,经济利益来考虑。文化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教化功能,让人们了解敦煌,通过敦煌让人们认识中国古代的文化、艺术,这种作用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观众中有很多老人、小孩,普通观众,他们不一定全能看懂,但其中有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过去我们的教育不太得当,像用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给人以视觉享受和美的震撼的形式就很好,其次是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播,正是因为佛教的信仰,产生了古代悠久、灿烂的文化。
此次观众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从规模、效果看,都是空前的,这种展览的盛况也是美术馆建馆以来最好的,展览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从中也可看出现在人们在物质欲望满足之后,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和追求。这是个可喜的现象。和别的艺术形式不一样,石窟是多种艺术形式综合利用的成果,敦煌石窟前后延续十四个朝代,1000年,10个世纪,从十六国时期直至元代,中间几乎没有中断,有4.5万平方米绘画,做成1米高的画廊,可以绵延45公里,时间跨度之长,壁画面积之大,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仅彩塑就有2300多身,表现得很细腻,精致,这是其他石雕像所不能比拟的。
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绘画、雕塑等等,离开石窟就无法谈,石窟中也有很多古代物质文明的反映,如农耕,狩猎等,保留了非常多的形象的历史资料,这是文献记载所不能替代的。这就是敦煌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石窟之冠的原因,再加上藏经洞发现了大量经卷,其学术、艺术、历史、文化价值在国际上都没有可替代性,至今热度不减。甘肃今后在对古代文化的宣传方面应加大力度,敦煌在海内外有不可替代的魅力,是甘肃一个很好的名片,也是宣传甘肃的一个很好的窗口,怎样利用好这个资源,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为宣传甘肃和甘肃的经济发展做贡献,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值得好好研究。
女,满族,浙江杭州人。1931年3月生于法国里昂,1937年回国。是我国著名的艺术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教授。1945年至1948年在甘肃敦煌随其父常书鸿学习敦煌壁画艺术。1948年赴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学习,1950年回国。1951年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工艺美术教研组任助教。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在首都北京能搞这么大型的展览我感到非常高兴,从开幕式,到开讲座讲课,陪同事、朋友去,我先后去了5次,每次去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总的来说很感动,敦煌艺术展览在北京举办过几次,第一次是1951年在故宫,周总理要求我父亲常书鸿举办,当时影响很大。这次是21世纪举办的非常成功、引起轰动的展览。因为敦煌艺术历经10个朝代,延续1000多年,在世界上是仅有的。京城不同层次的老百姓都来看,这是个好事。但我也有担忧,这样不能很好地欣赏,如此拥挤对复制品也不好,敦煌研究院此次下了狠心把老底都搬来了,这些临摹品本身就有文物价值。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我父亲那一代老一辈人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任何报酬,执著地投身洞窟临摹、保护工作,他们认真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历史、文化、作画程序,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地进行临摹,对壁画非常小心地保护,并且创造出了客观临摹、整理临摹、复原临摹三种方法,为以后的敦煌壁画展示、研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现在看到的临摹品都很珍贵,反映了当时那一代人对敦煌艺术执著的热爱和认真的工作态度。现在如此拥挤,会对摹品造成影响。由此想到现在国家对博物馆免费开放是一件好事,可以给民众提供一个更好地接触优秀文化、欣赏艺术、接受教育的机会,但也不能简单从事,应该有更详尽的考虑,包括对藏品的保护和人员、卫生间等设施的配套等。莫高窟同样存在一个保护问题。2006年在控制人数的情况下还有参观者55万,这些文物已延续1000多年,迟早要衰老、要损坏,但我们应想方设法延长它的生命,如何将宣传、弘扬和保护有效地结合起来,今后应当好好考虑。
1956年生于沈阳,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曾任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主任、学院副院长、《美苑》杂志副主编、中国画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此次展览在京城引起轰动,举办得相当成功,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遵照这个精神,中国美术馆和敦煌研究院都认识到应当以此为契机宣传、弘扬敦煌这个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及时进行筹划,周密安排。
文化部领导对此也非常重视,把这个展览列入2008年奥运文化重点项目。两院在筹展、布展、配套服务、讲解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我作为主要的筹划者和组织者,非常感动。此次展览的内容包罗万象,非常丰富,既有史料性、思想性、艺术性,又有趣味性、可观赏性。展览形式非常新颖,力求普及化、大众化、鲜明化,体现了美术场馆展览式样的主动性。我们办馆的宗旨,就是一切从观众的立场考虑问题,一切以人为本。展览中敦煌研究院配备了一批讲解员,成为展览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观众们对讲解员的讲解反映都非常好,他们来到这里近两个月,春节都没有回家,始终坚守在岗位上,非常辛苦。
敦煌艺术品的属性,是不可移动的,展览的临摹品是敦煌研究院几代人半个世纪用一生的心血完成的,他们历尽艰辛、数易寒暑,艰苦奋斗,使这些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穿越时空与现代人产生共鸣,应当向这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1960年生于天津,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唐研究》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编委、《中国学术》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汉唐中西文化交流、唐五代西北民族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文书、敦煌古籍整理研究,著有多部专著。
展览完整地再现了敦煌石窟艺术,对于我们了解莫高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另外它本身就是艺术品,给人以美的享受,是研究院几代人心血的结晶。它们不一定就是对洞窟完全的复制,其中有他本人的理解、创作,如张大千、段文杰等人的作品,敦煌石窟本身不能搬运,内地的老百姓去一趟也不容易,此次展览是对敦煌艺术的弘扬,非常不错。敦煌学的形成,敦煌艺术本身被世人所重视,是缘于藏经洞的发现。
当时敦煌本身是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咽喉之地,明代以前非常繁荣,因此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从汉代开始,河西走廊开始繁荣,至唐代达到鼎盛。1900年发现藏经洞后,敦煌艺术才被世人慢慢知晓。藏经洞是莫高窟的一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藏有上起三国、下迄宋代近10个朝代的五六万件历史文物,内容包罗万象,除了佛、儒、道和其他宗教经典外,经、史、子、集、诗、词、曲赋、通俗文学、水经、地志、历书、星图、医学、数学、纺织、酿酒等一应俱全。
其中封存的东西里还有稿纸、绘画稿、榜题、底稿等,对当时的画家,在敦煌文献中有大量记载,包括供养人、出资人等,研究、欣赏敦煌艺术二者是不能分开的。此次展览的观众主要还是普通老百姓,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集中观赏的机会,因为大部分人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去一趟敦煌。2000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时就有很多人,此次展览的学术含量、艺术含量都更高一些。如今国人因为网络、图书的发达,对传统文化的了解都很深,有很多人在参观展览之前都要上网,买一些相关图书来看,说明中国大多数人的人文素养、文化水平在提高,读书人越来越多,我们应当给他们多提供一些高水平的精神文化产品。
山西屯留人。擅长油画、壁画。1982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任地区文化馆美术组组长。1989年入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日本画科平山郁夫工作室学习,获硕士学位。现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这个展览是从现存的2000余幅单幅临本中抽出的最精华的部分,大部分作者都有20年以上的临摹经验,复制的洞窟总共有13个,此次展出了10个。通常一个洞窟需要15个人画4年才能完成。
此次选择展品,除了考虑选择莫高窟1000多年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将作者的代表性和艺术观赏性放在了首位。这个展览是常书鸿、段文杰、史韦湘、关友惠、潘洁兹、李振甫等几代人用心血和生命打造的,莫高窟是个没有作者的世界艺术宝窟,而这个展览是有作者的,绝大部分人是有着巨大艺术天份的,他们舍弃了很多东西来到这里,怀着一颗虔诚之心进行临摹,可以用“卑躬屈膝”这个词来形容,就是因为他们完全被这些优秀的祖国文化遗产的魅力所征服了。
从老一辈到现在的中青年画家,都是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自投罗网”,这批人非常了不起,能够真正体现甘于寂寞,甘于奉献,忘我无私的敦煌精神,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江苏宜兴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8年毕业于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后历任军事工程学院助教、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研究室主任、研究所副所长,国防工办副局长,国防科工委科技部副部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二届理事,中国航空学会第二、三届理事,国防科工委副主任。
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晋为中将。到敦煌莫高窟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第二次是全国人大考察,大约是在2000年。去年想去,79岁了,身体不行。这次展览不简单,印象最深。把多少洞窟、多少年代贯穿起来了。
这个古代文化艺术,是几千年保存下来的,现在不但要保存,还要复原、创造,我觉得把古董变活了,让古董回到了现代人生活中。另外,看到的文物,从莫高窟整体来看,保存技术、观念,都有很新的变化,人才也具备了,挺好。敦煌,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经过多少年的研究,有研究的人才,有历史性的基础,比较难得。
我们应当重视古董文物,去了解,开发它。我们志愿者讲解员共有六七十人,有在国博、首博、中华世纪坛各处的,此次都汇聚到美术馆来了,因为我们对敦煌文化都是情有独钟,就是因为它太有魅力了。敦煌是祖国特有的瑰宝,虽然比较深远,但人们都为它的魅力所吸引。我在给参观者讲解时,发现观众最感兴趣的还是其中的宗教思想,我通过讲解前的准备了解到很多佛教知识,通过古代丝绸之路,古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成为不同朝代老百姓心灵的安慰剂和精神寄托。
宗教中蕴含的一种真、善、美的东西,以非常通俗的形式展现出来了,迎合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思想。在北京,有很多不同时代的佛教文化遗产,如景山的五佛寺、颐和园后的释迦多宝琉璃七层宝塔、动物园后的五塔寺等,有很多都可以结合敦煌石窟艺术来讲解。通过两个月的讲解,我得到了前几十年都未得到的东西。尽管相当累,但两天不来心里就痒痒,感谢甘肃人,感谢敦煌人,大家都对敦煌的保护神充满敬意。